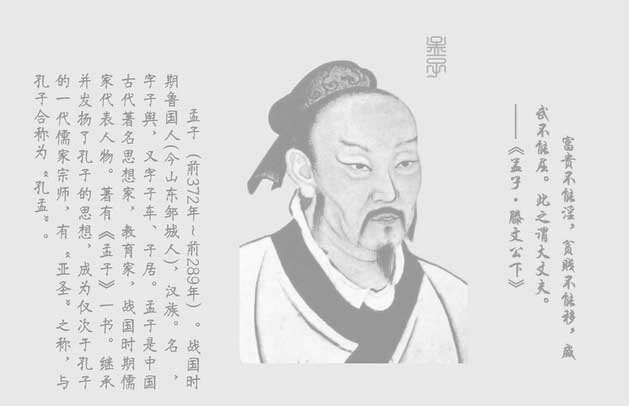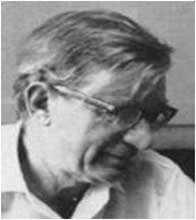
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矛盾中儒家尝试与西方融合_HellmutWilhelm著
热度: loading...
作者Hellmut Welhelm (卫德明) in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ion. 译者 新浪名高中和,百度名all4you3,博客gao-zhong-he.github.io,欢迎探讨。已经翻译《Tseng Kuo-fan in Peking曾国藩在北京 1840-1852:他的经世和改革思想_Han-Yin Chen Shen著》、《曾国藩和刘传莹_卫德明(Hellmut Wilhelm)著》、《The background of Tseng Kuo-Fan's ideology曾国藩思想起源+Hellmut Wilhelm卫德明教授》。虽然是写于几乎一百年前的文章,但是对当下仍然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比如,关于西方科技在中国总会遭遇强大的阻力,中国社会中总是存在一种惯性和惰性。再比如朱熹认为集权的社会结构是不可能应用西方的科技、机构、思想,这个观点正确吗?如果能应用,那么能到什么程度?这都是探索了一百年,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请有识者细品此文。
王先谦是中国著名的学者,他在一封给Pi Jung-nien的信中评价了19世纪的中国对西方思想和技术的反应:
【日本的改革发端于制造,中国的改革发端于辩论。他们获取浮名,谋取私利。空话满天飞,行动的种子却没有落地发芽,一切仍然保持空白,没有任何出路。】
我们可以肯定王先谦是一个反对变革的人。但是,他的反对不仅仅是基于民族自大和仇外,而是基于对西方、日本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基于民族心理的起源的分析。东方社会的惯性,以及中国社会对新的发展的抵抗力,对他的影响是:改革是完全不可取的。因为他不去想像中国社会会产生变化,所以必然地厌恶一切有关改革的讨论,以及一切变通地从西化中获得实用效益的尝试。
当时不仅仅只有王先谦持有这样惊人的保守立场,另一位学者叶德辉试图通过他的理论反对一切西方的思想:
【亚洲位于地球的东南,而中国又位于东南的中心。如果说华夏和蛮夷没有区别的话,那么是否也可以说东方和西方也没有区别呢?(作者的意思是华夏显然优于蛮夷)在四季中春夏总是来得更早;在五部中,东南方的部是居于首位。这些都是人人皆知的事,但是中国人不把外国人认为是蛮夷。在五色中,黄色属于“地”,而“地”是位于正中的。西方人称呼中国人为黄种人,就意味者造物主给予了中国人最重要的位置。当西方人嘲笑中国人并放肆地对待我们,他们怎么会不想想以上这些道理呢?如果说中国和外国的地位差别是由国家的大小、强弱合理地决定了,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当周朝衰亡了,他们的王却保留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尽管鲁国比吴国、楚国要弱小得多,儒家都自称“鲁”的原因。而且这些道理是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
在中国有两种思潮反对西方在技术、机构、思想方面的影响。一派是基于社会经济层面,认为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尝试通过工业、商业来发展经济是行不通的。另一派是基于制度层面,在一个集权结构的社会中是不能应用的,朱熹是这个观点的创始者和代表人物。
但是在中国十九世纪晚期的大背景之下,许多的学者抱有(对西方)不妥协的态度,逃避进了象牙塔。虽然一些政治家在强大的保守思想作用下仍然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特有的方式来行事,但是大多数掌权的官员更加现实,觉察到他们那个时代的危险局面。十九世纪西方撞击了中国,在军事、经济和思想三个层次产生了影响。军事上的危急使掌权官员迅速发起了洋务运动。无论是应用西方武器和技术,还是吸收西方思想,掩盖在其下的根本动机是努力赶上西方神秘的军事力量。任何认可西方的人(哪怕是一丁点)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对国防构成威胁。
西方的技术和思想适应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那些不管是主动或者被动负责维护中国的“本”的官员要抵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入侵,他们发现他们自己被允许,有时甚至是被呼吁拥有更大的地方实权。尤其在太平天国(1851-1864)以后重心已经由中央逐渐开始向地方转移是显而易见的。服从个人命令的地方部队;个人建立和控制的军工厂、造船厂和工厂;个人对上流社会的影响力;个人对税收的分配和处理,所有这些因素都显示地方对北京的依赖性的降低,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并且使更多人忠诚于它。因为朝廷对传统管理的失败,瘫痪的管理、溃败的军队,所以由于发展国家的需要,权力自然下移到地方官员身上。因为地方官员出于责任拥有了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因素的权力,所以有机会将个人的观点转化为国家的战略。
在这个背景下西方的科技得以应用,顺理成章地西方的思想也得到推广,但是这些行动很多时候都只是做为政治游戏中的砝码而已。地方官虽然打着为国家发展的旗号,但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发展而是借机实践个人的利益的增长。朝廷当然不会任由地方权力自由膨胀,它也采取了和地方相似的策略:开辟新的财源,雇佣外国顾问,尝试接纳西方思想。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朝廷甚至赢得了曾经失去的一些优先权。高官们不得不为了迎合朝廷的旨意而选择自己的立场(进行西化),但是大量的构想的项目在矛盾冲突中夭折。人尽皆知的故事是关于雇佣一支海军中队,包括全部指挥官和队员。它历经困难后还是驶到了中国,但是由于指挥官对中国权力结构的不了解,不能臣服于地方官的监管,最后被迫回去了。或许应该提及中国对美国派出的公费留学计划,它让上百个中国学生到了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但是在八年之后这些学生即将达到预期目标时被召回,因为李鸿章意识到被浸淫美国文化的孩子的忠诚可能不在他这儿,而是被引导到了另一个地方。
地方和中央的大部分官员都在外国顾问和中国助手的帮助下引进了西方的思想给中国知识界。除此之外,许多中国学者和独立个人也再完成相同的工作,尽管他们不得不和官场以及外国人联系,或者推销自己的理念以获得声名,但是他们对有启迪的思想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传播西方知识。
有一位叫魏源的人,他曾是林则徐的幕僚。他的《海国图志》一书问世于1844年,这本书是在林则徐自己所编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的,《四洲志》主要汇集了外国的报纸和杂志,它向中国知识界引入的外国知识是极为准确的。在它的引言中有这么引人注目的一段:“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容闳是第一位从美国回国的学生,他负责介绍西方的制造技术,成为江南制造局的奠基者,后来促成了上文提及的首批公费赴美留学事件。王韬是从英国返回的留学生,是杰姆-理雅各(James Legge)的合作者,他非常清楚世界大事和西方制度,这些都是通过报纸广为传播。还有数学天才李善兰,最初他和伦敦传教士协会的Edkins、Wylie、Williamson一起翻译西方著作,包括代数、地理学、天文学、机械学和植物学,他独立撰写了《对数探源》。李善兰曾经做过曾国藩的幕僚,后来被聘为同文馆的导师,同文馆是帝国的一个学院。还有一位辜鸿铭,曾经是张之洞的幕僚,对西方的哲学和文学有较深的了解,逐渐使它本能地捍卫中国文化,把本来浅薄的东西描绘得极为眩目。其它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生带回的见闻形成了一个大的潮流,也促成了清朝首次向外国派驻外交官,如郭嵩涛、曾纪泽、薛褔成。
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外国教士以及传教会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及的伦敦传教会已经在海外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由William Miline在1821年建立的位于马六甲的英华(Anglo-Chinese)书院,后来转移到了香港,它的医疗工作被广泛认可,而且印刷品的流通量很大。莫里逊(Morrison)教育会在1835年成立,容闳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实用知识传播协会成立于1835年,后来的克里斯蒂安文学会有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通过使用中文编写的报纸《万国公报》和一系列翻译作品。成立于1879年的圣约翰学院成为西方教育的又一个标志。伦敦的泰晤士Times报在1863年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号召传教士的工作“应该将介绍西方文明放在首位,只有当文明开化到一定程度才能教育当地的民众。”相似的文章也出现在美国和英国的其它报纸上。一大批在中国的传教士响应了这个号召,他们重点关注学者、官员而忽视对下层人民教育。上文提到的组织和独立的个人传教士的努力对西方思想传播起到巨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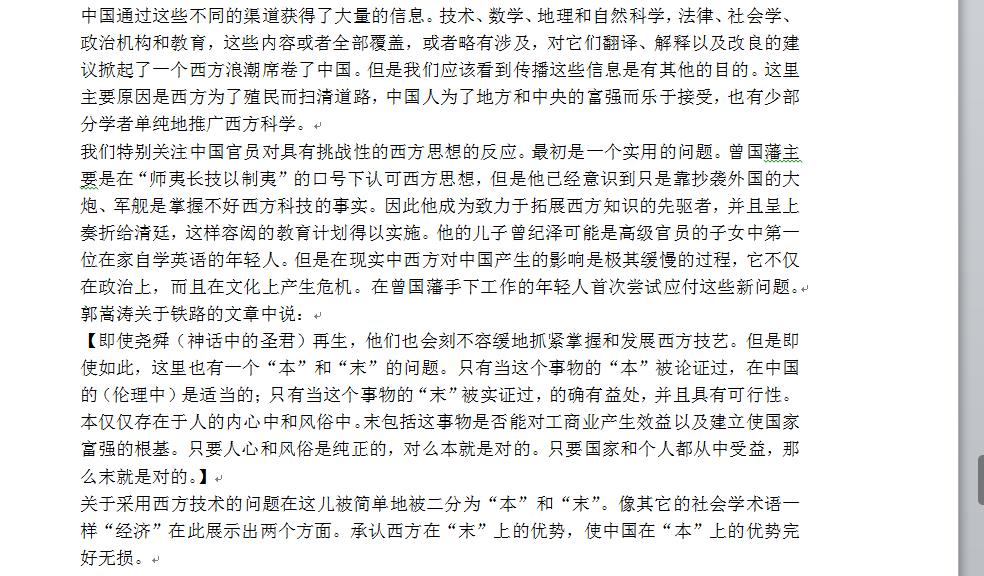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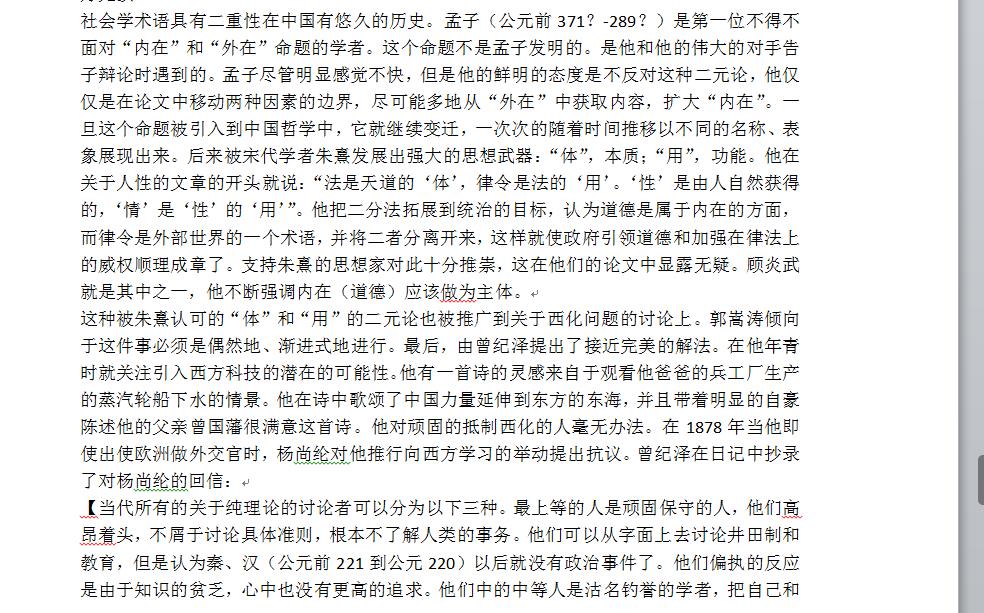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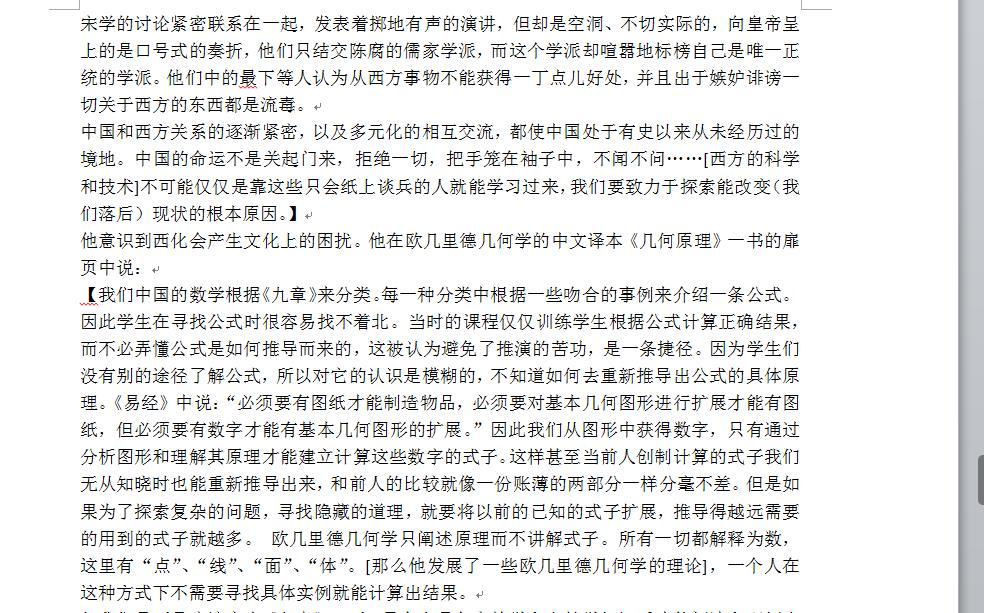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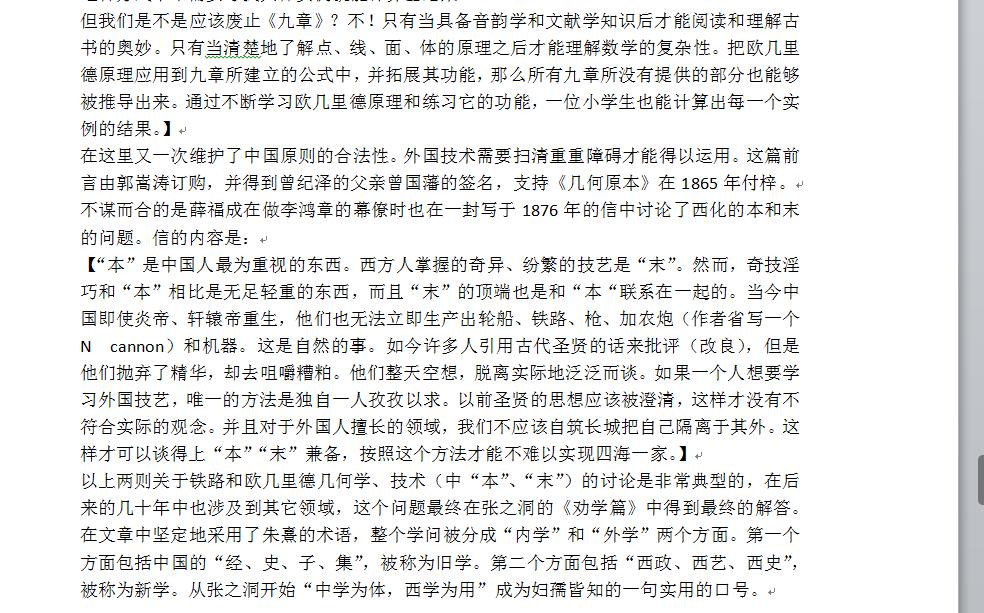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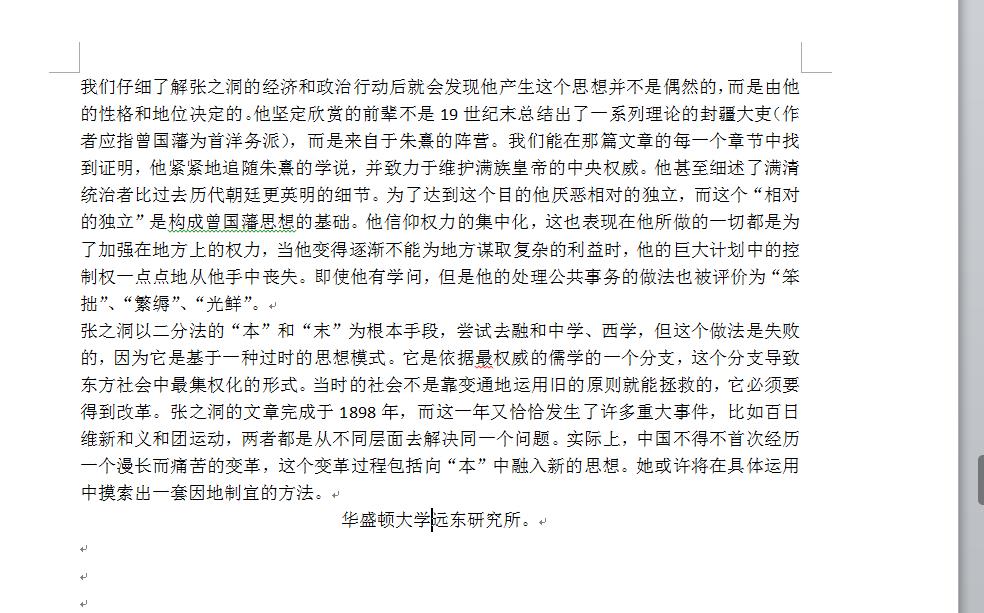
发表于2011年
附上作者的资料,引自https://www.goodreads.com/ 作者介绍Born in Qingdao, China
December 10, 1905
Died July 05, 1990
Genre Religion & Spirituality
Hellmut Wilhelm was a German sinologist noted for his broad knowledge of both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history. His father, Richard Wilhelm, was also a noted sinologist.
Wilhelm was an expert on the ancient Chinese divination text Yi Jing, which he believed to represen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hought. He also produced one of the most widely-used German-Chinese dictionaries of the 20th century. He held teaching positions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